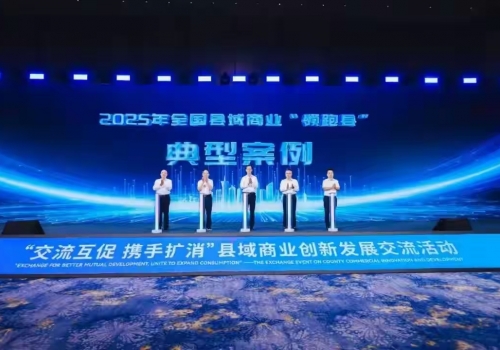一、风雨三百年,一桥载山河
兴隆山卧桥并非普通桥梁。它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,由知县唐鸣钟主持修建,初名“唐公桥”,后因屡毁屡建,历经嘉庆年间的“迎善桥”、光绪年间的“云龙桥”等名,最终以“卧桥”之名融入陇原文脉。桥长23.6米,横跨栖云、兴龙两峰深谷,以“伸臂木梁”结构闻名——全桥无桥墩支撑,仅凭层层叠涩的木臂卯榫咬合,如巨人挽臂凌空飞渡,被桥梁泰斗茅以升誉为“中国伸臂木梁桥的代表”。其廊亭彩绘、琉璃瓦顶与道家“云龙相生”的哲思交融,楹联“云比泰山多,霖雨苍生仙人悦”更道尽其在自然与人文间的精神纽带。
卧桥断,文脉续。
2025年8月7日,榆中县遭遇有记录以来最强暴雨,兴隆山单日降雨量达220.2毫米。山洪如怒龙席卷峡谷,这座省级文保单位在浊浪中轰然垮塌,碎木残瓦随激流奔泻。物理的桥虽逝,文明的桥却因灾难而愈发清晰——它承载的不仅是行人脚步,更是三百年匠艺智慧、道家天地观与西北民间艺术的结晶。

二、“不能消失”的誓言:从废墟中打捞文明基因
灾难次日,甘肃省文旅厅厅长何效祖在网友评论区的回复引发关注:“我省2019年修复桥的图纸都在,受损架构已收集,这一历史文物建筑不会消失,也不能消失!” 短短数语,直抵文物修复的核心矛盾:原真性与延续性的辩证统一。
据史料记载,卧桥曾多次毁于山洪,又因“屡毁屡建”的执着延续文脉:
1900年,甘肃布政司拨银千两重建,以“云龙”为名强化其沟通两山灵气的象征;
1989年为抵御自然侵蚀,桥体被注入钢筋混凝土“现代骨骼”,却仍保留木构形制;
2019年的修复图纸与今日残骸共存,为“原址原貌”重建提供科学依据。
兰州市文旅局回应“先救灾,后修桥”的务实态度,更凸显保护逻辑的优先级:人命重于器物,但器物承载的文明重量同样不可弃置。
三、重建之思:在敬畏与创新间寻找平衡
卧桥的重生之路面临三重担心,一是技艺传承的挑战,纯木构伸臂梁工艺濒临失传,能否以传统榫卯复刻“无钉无铆”的力学奇迹?抑或需借现代材料加固结构?二是生态关系的重构,作为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设施,重建需统筹山洪防治与生态保护,避免“修复即埋隐患”。三是防灾体系的升级,此次山洪暴露极端气候下文物脆弱性。未来是否需建立文物灾害风险地图,将防洪、防震纳入文保日常?
何效祖厅长的承诺背后,恰是甘肃文旅近年直面灾害的缩影:2023年积石山地震后,他带队通宵排查炳灵寺石窟等文保单位险情,开创“应急评估—临时支护—分期修复”的灾后文保流程。卧桥修复,或将成为甘肃探索“预防性保护”与“韧性重建”的范式。
四、甘肃文旅的“卧桥时刻”:从文物修复到文化自信
卧桥之殇,恰是甘肃文旅重塑形象的契机:从历史维度来看,它串联起榆中八景、陇右道文化,修复工程可联动周边混元阁、大佛殿等遗迹,打造“兴隆山文化廊道”;从精神维度上讲,“屡毁屡建”的坚韧与厅长“不能消失”的宣言共振,呼应“坚守大漠”的莫高精神,塑造甘肃文保新叙事;从产业维度来分析,作为游客进入兴隆山的咽喉,卧桥重建可推动生态旅游与文化遗产活化融合,使“云龙复现”成为文旅复苏的文化符号象征性事件。
断桥处,长虹将起。
山洪能摧垮木石,却冲不散文明的韧性。从乾隆年间的知县唐鸣钟,到今日承诺“不能消失”的何效祖,守护卧桥的接力跨越三个世纪,本质是对文明延续性的集体宣誓。当重建的锤音再次响彻峡谷,新生的卧桥必将超越物理形态,成为今人回应历史、敬畏自然、启示未来的精神地标——它卧于山河,更立于人心。
“文物修复不是复刻过去,而是以过去之魂,筑未来之桥。” —— 这座桥,甘肃修给世界看。(作者:也很美)